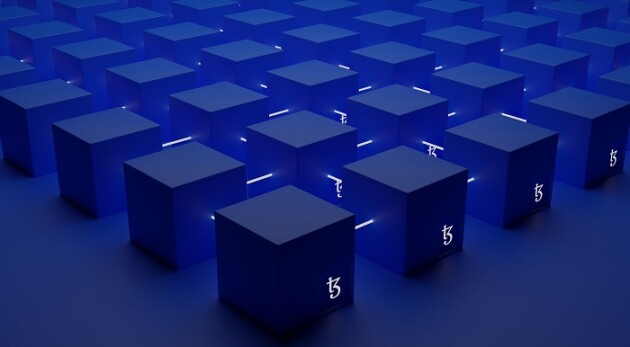怎样造就一部被广泛讨论的现象级电影?最质朴但也是最卖力的办法可能就是摆出社会现实。说它卖力,是因为在无评级的审查制度下,社会现实并不是那么好摆——至少徐峥改过两次片名。这导致《我不是药神》成为了一部非典型的左派电影。《药神》保有左翼最基本的关怀:对政府、资本、最终落实到社会不平等的不满。但它并不像主流的左翼那样直达现实最疼痛的地方:很容易注意到,影片结尾传递的最基本的信息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但这显然不是导演组的最终判断,《药神》想指桑骂槐,曲线救国,敲山震虎。所以它的内核也不是中国当今声势浩大的新左派,后者在政治光谱上的站位要保守得多。我想它为后来的左翼电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表明了电影的基本立场后,我们回到正题,来聊聊它关心的问题。(a)为什么正版药这么贵;如果(a)的理由成立,那么(b)为什么印度能卖便宜的仿制药,而中国不行;(c)如果中国接受(a),但是又不愿接受印度的理由(b),那为什么最终将抗癌药纳入医保;(d)上一个命题有没有带来什么更大的疑惑?接下来我将按顺序讨论以上四个问题。
(a)“黑心无良药商?”:为什么正版药这么贵?
《药神》中的瑞士公司当然有它自己的理由。很容易想到,研制一批新药的成本极其高昂。以美国为例,如果要开发一种全新的药物,所谓的“化合物筛选”是第一关,医药公司新合成或发现的化合物只有1/1000的概率能进行临床试验,最终像“格列宁”这样上市的化合物只有1/5000。由于显现药效需要时间,观察副作用需要更长的时间,临床试验一共有三次,最终的审批还要慎之又慎,单单一种新药的开发至少持续10年,耗资接近30亿美元,更谈何实现盈利?如果资本想要挣钱,价格抬高是必然之举,这也就是被聊烂了的市场和商品的关系。很多人会想到为什么不让国家接手药物研究,我们将在(c)回到这个问题。
(b)“印度是穷人的天堂?”:为什么印度允许卖仿制药,而中国不行?
仿制药的优点在于价格,由于省去了漫长的研究时间,它的成本比正版药低得多,还是市场的基本原理:它没有理由卖得贵。所以问题实际在于,印度政府为什么能允许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似乎只有功利主义能为之辩护。众所周知,无论是行为、间接还是规则功利主义,最终的决定性原则都是:“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其中自然包含降低最大多数人的痛苦。我们大可把什么是幸福放在一边,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仿制药会给病人带来幸福,给研发者带来痛苦。功利主义坚持所有人的偏好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只要病人比研发者人多,或者他们的对仿制药的渴求比研发者对其的规避程度更高,仿制药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上面两个理由都必然成立,病人等药救命。
可能很多人都了解功利主义的问题,但我希望能把讨论范围限制在药业之内,毕竟在现代没有一种原则能为一切辩护。功利主义非常有效,它甚至能区分张长林和程勇:前者的行为不是道德的,因为他本可以像后者那么行事。但仔细想想,应用在药业的功利主义原则无论如何都会自我瓦解。第一,如果这种制度大规模推行,顶尖抗癌药的研发必然陷入停顿,功利主义者隐藏的论证前提是“存在一种药”,否则它将违背所有人的幸福,从而自我崩溃。第二,功利主义原则要求程勇一分钱不赚,单纯把药发给病人。因为程勇只是一个人,病人却千千万万。同理,这将导致没人买药,也导致原则的自我瓦解。功利主义的问题被称为“生活疏离”,它的要求太高了。一些间接功利主义者论述说,如果遵守法律和市场的规则,就能规避上面的问题。但这样一来,功利主义就自然失去了它的激进性,印度政府不能以此为自己辩护。有趣的是,站在全球化的角度看,功利主义的全球正义是可行的。美国患者在墨西哥买药,印度则是世界仿制药中心,将仿制药限制在小部分地区,却默许它供应较大的市场,避免前述问题就可能了。
但一般而言,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不像上文那样从内部出发。而是采取更简单的思路从知识产权出发为之辩护,进一步说就是洛克的方法。简单说来三步走:我对自己拥有自我所有权,知识和财产都是由于自我产生的,所以我对这一部分知识和财产有所有权。洛克为此给出了五个证明,最著名的是“劳动渗入论”,举个例子,你在种地的时候把劳动渗入到了产品中,所以它是属于你的财产,其他的同样符合这个原则。诺齐克对此有一个著名的反驳,如果你做了一罐番茄酱,用力把它倒进海里,是不是说它们弥漫的地方就是属于你的?洛克的论证灌水太多。至于为什么我们如此能接受最右的自由主义者都不能接受的说法,应该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论证剥削的两条路径,一是异化,另一个就是自我所有权。其实二者的核心问题意识极其接近,只是前者偏向黑格尔,二者靠近古典自由主义。
(c)“你能保证一辈子不得病吗?”:如果中国能接受专利权,同时反对功利主义的论证,那有什么理由将抗癌药纳入医保呢?
这个问题十分反直觉,尤其对于看过电影的人。当我们随着镜头穿过参加吕受益葬礼的人群时,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将其纳入医保?医疗保险和将企业交给国家实际上是一体两面,都是大政府介入市场的基本方式。但是有很多人都对此提出了很深刻的怀疑。
姑且放过波普尔和哈耶克不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反极权主义,和我的讨论并没有太多关系。值得重视的是诺齐克的观点,如果我拥有对财产的绝对权利,又有什么理由把纳税当作义务呢?如果我并没有患病,为什么要把我赚来的钱给别人治病?这难道不是一种强迫劳动吗?如果我自己患病享受到了医保的福利,可能就会有像电影中老太太那样问:“谁能保证一辈子都没病呢?”或是“谁家没个病人”。公平对当原则一种可行的责备,但我依然可以振振有词,这并不是我真正的想法,而是被逼无奈的,医保的起点本身就不公平。所以在诺齐克看来,有财产权的人接受保险简直是天方夜谭。
如何驳倒诺齐克,维护我们的直觉呢?德沃金或许给了我们一条思路。诺齐克认为他对自己自然的天赋得到的财产拥有充分的所有权,令人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反思自然天赋从何而来。世界上最具偶然性的就是出生了,像我这样生来健康的人是不是比那些生来患病的人更有资格享受健康呢?像我这样至今没有得白血病的人是不是比那些患者更有资格享受健康呢?一定不是的,因为在出生之前,未来之人从来都不存在,更不可能获得资格。那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要为生活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享受普通人能享受的生活呢?伦理学上习惯于称此为“运气”,它是绝对的偶因。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要尽其所能地做到境况的平等,再允许人去选择自己的生活,让所有人都有成为所有人的可能性。德沃金的方法就是“保险”,放入我们正在谈论的医疗体制,也就是说要“为健康担保”。健康者拿出的这笔款项将被用来服务患者,或者是未来的患者——当然,可能就是你自己。总体来说,德沃金的说法可能是对医保的最佳辩护,比起单纯的直觉和道德论证有说服力得多。
(d)“这世上只有一种病?”:上一个命题背后还有些别的什么吗?
熟悉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这些名字的人可能清楚,过于细化的医疗保险在他们的思考中根本没有位置,这些人关心的是“正义”问题。放在西方的语境下,也就是“什么人配得到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时候不平等是可能的?”《药神》想讨论的也不仅仅是医疗问题,借张长林之口,说:“在我看来,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有心者可能会注意到电影中随处可见的东方明珠和白血病患者居住区的对比,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这种现象都广泛存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部分的失调实在太常见了,每个大城市中都有零星的“城中村”。在城市生态系统里,它们就是排水沟——这似乎在说,它们必须存在,要不垃圾和脏水往哪里泼呢?低端人口往何处摆呢?
我们聊到了点子上,从城市空间的分布位置能够清楚地了解到社群在城市中的地位,当然,还有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习惯于作伪先验论证:如果没有这些人,脏活累活就没有人做了,中产阶级也不会感到紧张而努力工作了……他们却没想到,自己证明的只是不平等的必然性(物质资源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除外),而不是一部分人生来高贵,一部分人生而低下。或许我们不必使用“生而”这种煽动性词语,但至少不能让一个人因为一次偶然的疾病而失去了一切选择。《药神》背后,讨论背后,医疗背后,是有目共睹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这个问题,点到即止。
原文链接: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9499136/